在革命中戰斗成長,在她心中母親就是那一株小草
我的母親裡凡,原名汪玉雯,曾改名汪雯、黎明、裡凡。母親1923年出生,因幼年喪母,從小跟著外祖父長大。
母親讀完小學后,家裡無力再供她讀書,便去了縣裡一家醫院當學徒。那時,外祖父年事已高,身體不好,沒有辦法繼續照顧她。於是,母親隻好回到她父親和繼母身邊。
1939年冬的一天,母親正在家裡做飯,她的女同學朱劍英突然從門外風風火火跑進來。朱劍英一進門就壓低嗓門對她說:“你不是一直想參加抗日打鬼子嗎?你收拾一下,今晚來古河鎮(今屬安徽省全椒縣)找我!”
朱劍英說完,就匆匆離開了。當晚,母親帶上幾件衣服悄悄離開家,直到天亮時才找到朱劍英。朱劍英當時在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工作團工作。就這樣,16歲的母親加入了工作團,並改名汪雯。
母親工作積極性很高,唱歌、跳舞、演抗日活報劇,渾身有使不完的勁。她有時看到朱劍英神神秘秘地外出,問她去了哪裡,朱劍英也不說。母親有些不高興,就去問團裡的“老大哥”吳谷泉。
母親不知道,吳谷泉其實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,朱劍英也參加了共產黨。吳谷泉了解母親的工作表現,告訴她想真正抗日就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。母親表示願意加入他們的工作。從此,母親宣傳抗日工作的積極性更高了。
一次,遇到日本飛機轟炸,母親在躲避時,腳一滑掉進水田裡。幸虧吳谷泉在后面看到,他一手拽住母親,一手拉著朱劍英拼命往前跑,最終躲過一劫。在日常相處中,吳谷泉和朱劍英會認真耐心地給母親講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。母親心中埋下了信仰的火種,更加積極地向黨組織靠攏。
1940年春的一天,吳谷泉通知幾個已暴露的同志,當天晚上跟交通員撤退到根據地,其中就有母親。那天晚上,吳谷泉特意安排了一場演出,掩護大家撤退。等特務發現有人逃走再派人去追時,撤退的人員早已到了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,並且按地下黨的安排都改了姓名,讓追來的敵人無法找到。母親說,她不願意跟大漢奸汪精衛一個姓,就改叫黎明,並投入了工作。吳谷泉和朱劍英在革命工作中產生了感情。后來,他倆趁工作團換人的空當,借口回家結婚(他們后來成了我的公公、婆婆),離開了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工作團,到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從事經濟工作。
1940年8月,母親在安徽合肥六區工作隊工作期間,加入了中國共產黨,9月又奉令調到蘇北鹽阜地區,參加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工作。當時,阜東地區的一位校長孟友仁,常常夸獎母親颯爽英姿:“穿一身灰布軍裝,別一支小手槍,起早貪黑地動員群眾參加抗日,才17歲,又是女同志,不簡單不簡單!”
在阜東時,母親與另一名女同志張野萍,被安排住在村民周孝雲家。她倆經常給12歲的周孝雲講革命道理。有一次敵人偷襲,母親和張野萍都到區裡開會了,家裡隻剩下周孝雲。母親和張野萍回來后,沒看到周孝雲,兩人藏在枕頭下的手槍也不見了,急得滿頭大汗。好在沒過多長時間,周孝雲回來了。她說,發覺敵人偷襲時,立馬就想起了兩人的手槍,趕緊掀開枕頭,摸出手槍放進籃子裡藏好,然后跑進蘆葦叢中,一直躲到敵人離去。
那時,鹽阜地區群眾生活很艱苦,吃了上頓沒下頓,新四軍戰士也跟群眾一樣挖鹽蒿子充飢。由於吃得太差,營養跟不上,母親經常流鼻血。有一次,母親鼻血流得太多,臉色煞白。一位當地群眾就叫兒子冒著嚴寒,去溝塘邊挖了幾個茨菇煮水給她喝,才救了她一命。有時遇到敵人突然進村,群眾會急忙找便衣給新四軍戰士換上,盡力掩護他們。
1944年,母親被選調去鹽阜區委黨校學習。這時,她已改名裡凡。學習期間,她遇到父親曹嵐,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,兩人結了婚。第二年秋天,我的大哥出生。
那時,白色恐怖籠罩著根據地,很多干部群眾被殺害或被迫逃走。按照規定,母親本應該帶著我大哥撤退,但考慮到工作需要,她決定把我大哥托付給別人,自己留下來繼續斗爭。后來,大哥得了肺炎,沒有藥醫治,又趕上發洪水,等父親設法送來藥時,大哥已經死在母親的懷裡了。
淮海戰役開始時,母親懷上了我大姐。在一個大雪天的行軍路上,母親臨產了。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她扶到一堵矮牆內側,墊上被子——大姐就這樣出生了。后來,大家又找來一副擔架,抬著母親和大姐回到老鄉家休息。大姐滿月后,母親將她留在老鄉家裡,又出去工作了。
小時候,每次聽到母親講大姐出生的事,我總以為她是在編故事。直到我也做了母親,才更體會到她當時的不容易。
新中國成立后,母親在蘇南法院、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等單位工作過。1984年1月離職休養。
2005年,母親獲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。5年后,87歲的母親因病去世。她生前留下遺囑,不組織遺體告別,不給組織添麻煩,遺體捐獻給國家醫療事業。
母親晚年曾作過一首詩《小草》,表達自己的精神追求:“植根大地默無華,迎得春歸自發芽。晴沐陽光陰沐雨,朝披珠露晚披霞……脈脈含情描麗景,願鋪綠毯接天涯。”我想,母親就是那一株小草,向著她心裡的陽光,默默生長,一生無怨無悔。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- 評論
- 關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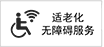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