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達勇:守島30年,向陽光而行

女兒的陪伴。

把軍裝穿成“皮膚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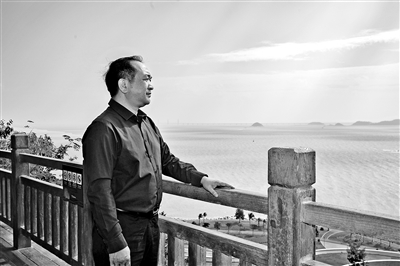
脫下軍裝的劉達勇眺望海面。

離別時刻。

劉達勇(右一)和“徒弟”一起勘察海上情況。照片由本人提供
陽光鋪洒海面,浪濤奔涌,拍打著島岸礁石。
劉達勇憑欄而立,望向遠方。
2021年新年第一天,辭舊迎新的日子,南部戰區海軍某觀通旅原雷達班長、一級軍士長劉達勇卻說不出再見。
這裡是野狸島。30年來,劉達勇每次都是從這裡登船,前往大海深處自己駐守的擔杆島。
幾周前,劉達勇退休離島。從那之后,他幾乎每天都會站在這裡眺望遠方。守島30年,曾經熟悉的風景,如今成為老兵生命的陽光。
離別
“把我留在島上,就是對我最大的照顧”
離開部隊頭幾天,劉達勇感覺心裡“空落落的”,那座小島和戰友的笑容總會浮現腦海。
“離隊前,旅裡准備為你舉辦個退役儀式!”2020年10月,第一次聽旅政治工作部主任任宏翰說起這事,劉達勇內心開始“不淡定”起來。
說不清是感動還是驚喜,劉達勇的第一反應卻是“拒絕”:“部隊年底忙,不能給領導添麻煩。”
劉達勇是全旅最老的兵,是戰友心目中的“老班長”。為他送行,是大家的一番心意。
10月20日,雷達站活動室,掌聲雷動。旅領導來了,駐地鄉親來了,和戰友們共同送別這位“兵王”。劉達勇的女兒葉子也專程上島接父親回家。
看著眼前一張張熟悉的面龐,劉達勇淚流滿面。葉子為父親認真整理“光榮退役”綬帶。從父親起伏的胸膛,女兒感受到了他內心的激動。
“班長你走了,我們會想你……”接過劉達勇多年積累的裝備維修操作筆記,雷達分隊長成廣帝泣不成聲。
此刻,劉達勇緊握著“徒弟”成廣帝的手,思緒穿越了時光,回到了30年前的夏天。
家住重慶涪陵山區,20歲的劉達勇還在區公所食堂學習廚藝。
“今年這邊要招海軍……”一天午飯,區武裝部長的無心之語,讓劉達勇的心猛地“震”了一下。海軍那身藍色軍裝,深深印在他的腦海。
“我去當兵吧?”下班后,他沿著山間小路飛奔5公裡回家,迎來的卻是父母的反對。
那晚,劉達勇失眠了。也不知哪兒來的勇氣,次日一大早,他再次向父母申明自己的決定后,報名參軍。
伴隨著悠悠汽笛聲,1990年2月底,劉達勇踏上了軍旅之路,他的人生從此轉折。
兩天輪船,從重慶到武漢﹔一整天的火車,抵達廣州﹔到部隊大院時,已是晚上10點。望著漫天流雲遮不住的點點星光,劉達勇心裡有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期盼。
3個月新兵訓練,2個月的觀通專業訓練,劉達勇樣樣拿第一。“那個年月,素質過硬才能去海防一線。”因為出色,劉達勇被分配到了戰備任務較重的擔杆島。
擔杆島位於伶仃洋海域,島上環境艱苦,但戰略位置突出。9月18日,劉達勇永遠記得這個日子。寒潮來了,他在珠海待了3天,才等到前往擔杆島的輪船。
歷經8個多小時的風浪顛簸,一個東西走向、形似“扁擔”的小島,隱約出現眼前。一隻腳剛踩上岸,劉達勇便覺天旋地轉,許久才緩過神來。
“你小子,准是暈碼頭了,多坐幾次船就沒事了。”前來接兵的班長陳自清呵呵笑著,接過他的行李,將他推上了卡車。
盤旋的泥土山路,七八個人一起擠住的“干打壘”房子,鐵架子床也是鏽跡斑斑。洗澡沒熱水,到了冬天,隻能趁著大中午出太陽的時候,嘴裡大吼一聲,雙手舉著水桶,把涼水往頭上一澆……
島上非常潮濕,東西收在行李箱裡沒多久就會長出“綠蘚”。一次,劉達勇把放在行李箱裡的錢拿出來在陽光下晾晒,被山風吹飛起,他隻能漫山遍野地追。
劉達勇是山裡走出來的娃,守島的日子雖然苦,他從來不抱怨。3年義務兵服役期滿,20個同批上島的戰友中,最終隻剩劉達勇這個“獨苗”。
這一留,就是30年。
常年潮濕的海島生活,讓劉達勇患上風濕病,一到陰天下雨就疼痛難忍。
好幾次,領導主動提出將他調出島去。他總是那一句:“把我留在島上,就是對我最大的照顧。”
擔杆島距離香港直線距離不遠,望海探空,劉達勇和戰友遙遙守衛航道安全。30年時光,他在一次次任務中踐行自己最初那句“用青春守島”的諾言。
1997年7月,香港回歸。站裡提前加強值班力量,劉達勇主動請纓,連續2個月包攬任務中最重的“凌晨2點至次日上午”的值班時段。
2008年8月,北京奧運會香港設分賽區。劉達勇推遲原定的休假計劃,一個多月在陣地值班。他比誰都認真,在他心裡自己和“祖國”第一次離得那麼近。
2017年7月,遼寧艦訪問香港。劉達勇以自己的方式一路護送“國之重器”駛進香港水域。
每一次夜晚值勤換班,走下戰位前,劉達勇喜歡在山頂上待一會兒。任海風輕拂臉頰,潮汐拍岸的響聲回蕩耳畔……
相聚
“你有你的堅守,我有我的堅守”
清晨6點,劉達勇習慣性起了床,燒水、做飯,再給妻子申鳳倒上一杯熱水。一會兒妻兒起床,她倆就能吃上剛出鍋的早飯,喝上溫涼的水。
退休了,回歸家庭。劉達勇一直有這個想法,他在外面守了一輩子,漂泊了一輩子,如今該是“靠港”的時候。
洗衣洗碗,掃地做飯,一應大小的家務活,劉達勇全包了。“丈夫”和“父親”的角色缺位太久了,他想補上。
不大的屋子,很是溫馨。劉達勇身著白色軍裝與妻子、女兒一起拍攝的全家福,挂在牆上。
切菜,點火,起鍋燒油……下午5點,劉達勇快速准備著晚飯。把蒸好的魚端出,淋上熱油,再撒一把蔥花。“齊活!四菜一湯。”妻子和女兒樂得合不攏嘴。
這看似普通的相聚,對於劉達勇和妻兒來說卻十分不易。
現在是80公裡,過去是1472公裡——重慶涪陵到擔杆島的距離。入伍之初,劉達勇很少想家。直到遇見同為重慶人的申鳳,他開始想家,想念遠方的她。一封又一封的書信,在那個年代是戀人眼裡的珍寶。
部隊接通了“市話”,打一次費用很高,每天通電話在那個年代“太不現實”。劉達勇堅持寫信,也堅持隔三岔五發射一次“電波”,發下來的工資一部分寄給家裡,他還會專門存下一筆電話費。
后來,海島有了基站,但信號微弱,時有時無。舉著手機,他邊走邊喊“喂,聽到嗎”,成了當時島上的“風景”。
擔杆島交通不便,遇上風浪,船隻停航是常有的事。當時,郵包一個月送一次。每個月初,劉達勇最多時能收到厚厚一沓信。愛人郵來的每封信,他都讀得仔細,生怕漏掉字裡行間的每一處細節。
那年,父親劉顯柱過八十歲壽辰,劉達勇早就請好了假。海上風雨襲來,所有航船臨時取消。劉達勇坐在宿舍,心情如風浪般難以平靜。
“回不去了……”在宿舍來回踱步,劉達勇望著窗外連連嘆氣。那年,劉達勇被表彰為“海軍十大杰出青年”。他的行李箱裡裝著一枚軍功章,那是他送給父親的禮物。
“既然他回不來,那我就趕過去。”女兒出生后不久,妻子申鳳就帶著孩子隨軍到了“離島最近的岸”——珠海,一個人撐起家過日子。
擔杆島上有塊石頭,島民稱之為“望夫崖”。島上本來島民就不多,男人白天外出打魚,妻子留在家中照顧。每到風大浪高的天氣,她們就會來到這裡眺望海面,等待丈夫歸來……
申鳳心裡,珠海這座陌生的城市,就是她的“望夫崖”——她和丈夫之間從此隔著一灣海。他們望著同一片海、頂著同一片天,彼此間的距離在牽挂中變得不再遙遠。
“你有你的堅守,我有我的堅守。”每隔一段時間,申鳳就會登上小島探望劉達勇。送去一些衣物,帶上戰友喜歡的食品。待不了幾天,又匆匆下島——家裡,年幼的女兒還需要她的照料。
“每天守著家,每天都像在打仗。”這是申鳳在電話裡,經常向丈夫抱怨過的話。
幼兒園早上8點開園,申鳳7點帶著女兒出門﹔下午5點放學,申鳳下了班趕過去總是“誤點”。她早出晚歸,實在趕不及,就委托老師幫忙照顧女兒。這種“忙到飛起來”的狀態,持續到女兒升入小學。
海島上的漢子,總是將感情深埋心裡。山一般的外表下,內心裡是水一樣的柔情。
“她的生活,這麼近,那麼難,可我在島上啥也做不了。”回憶過往,劉達勇滿是愧疚。
如今一家人難得的團聚,劉達勇倍加珍惜。他們的家,與妻子單位、女兒學校隻相距兩三站地遠。劉達勇執意每天早晚接送妻兒上班、下學。
對這一家人來說,距離只是地理位置上的坐標,心與心從來沒有距離。
牽挂
“那閃爍的波光,已然成為牽挂”
守島30年,最牽挂的還是那個島。
記得一次休假歸來,劉達勇與擔杆村村委書記黎喜一同坐船上島。甲板上,海風柔暖。
“如今島上數你守島時間長,你是真正的‘老海島’!”一陣笑聲過后,黎喜若有所思地說:“走了也一定再回來看看,這裡也是你的家。”
這裡當然是家。浪花翻卷,劉達勇思緒涌動。凝望著海面,他久久沒有言語。
臨走前,劉達勇把營區周圍的大小角落,走了一遍又一遍。在他心裡,這裡比家更熟悉。他走了,可他的根已經扎進了這裡的石縫。
去年11月,海上突發寒潮,通航船隻全部停航。劉達勇盼著這次還能像往年那樣一連數天不通航。因為不舍,他像個孩子一樣,每天數著日子,看手機天氣預報。
老班長心裡的各種“糾結”,成廣帝看得特別真切。
成廣帝是劉達勇親手帶的“徒弟”。18年前,他和29名新兵一起來到擔杆島,劉達勇是他們的雷達業務班長。
帶兵,劉達勇的“獨門秘籍”就是兩個字——真誠。
學業務,劉達勇“手把手”地帶,從最基礎的理論、雷達開關機開始﹔訓練,他要求非常嚴格,誰的成績“掉隊”,他每天盯著加練﹔值班,他大膽放手,越是難判的海情空情,越是讓“徒弟”自己處理。
“上機操作,需要膽大心細,本來以為自己有‘兩把刷子’,要不是劉班長坐鎮指揮指導,真不知遇上多少麻煩。”回憶最初值班的經歷,成廣帝至今心有余悸。
有了金剛鑽,敢攬瓷器活。這些年成廣帝進步飛快,下士第一年就能獨立上機值班。對成廣帝來說,劉達勇既是“師父”,又是值得信賴的兄長。
記得那年義務兵期滿,成廣帝本想退伍,劉達勇勸他留下來。2018年,成廣帝面臨晉升三級軍士長。“女兒剛出生,父母身體不好,家裡又沒人照顧……”成廣帝一臉愁容,跑去和劉達勇商量。
“你是家裡的頂梁柱,家裡的事必須處理好。但另一方面,部隊也需要像你這樣的骨干。”劉達勇告訴他,無論如何選擇,自己都是他最強的“后援團”。
因為熱愛,歲月不覺漫長。從入伍之初,劉達勇干了28年班長,一直到去年,他還在帶新戰士。他帶的兵,如今很多都已成長為骨干,成了班長。
30年堅守海島,送走一個個朝夕相處戰友的時刻,是他最不願面對的時刻。比劉達勇晚入伍2年的徐宏,是和他關系最鐵的兄弟。徐宏離隊那天,劉達勇愣是沒敢面對面送他一程。
戰友情深,告別總是艱難。就像徐宏所說:“兄弟就是你有事我替你擔著,你獲得榮譽我替你歡呼。”劉達勇心裡也是這樣想的,兄弟之間總是“無聲勝有聲”。
站在碼頭一側,遠遠看著徐宏登船,當送老兵的輪船鳴笛啟動的一瞬間,劉達勇淚流滿面。
離別的背后,也有久別重逢。“老戰友遍布全國各地,走到哪裡,隻要一個電話,他們一定會趕來見一面。”劉達勇笑著說,“很多地方都有咱連的兵,以后走遍天下都不愁。”
離別的背后,還有無奈的不舍。劉達勇舍不下他的“老伙計”——日夜值守的雷達裝備。
“唯有沉下心來鑽研,才能把雷達的脾氣摸透。”數不清的日子裡,就連走在值班路上,劉達勇想著的都是艦船批次編號、回波特點……
雷達裝備數次更新換代,劉達勇一次次從頭學起,一次次學在前頭。他摸索出的一套快速判情技巧,如今已在部隊推廣。
告別不是遺忘,只是揮手轉身,走向人生又一段旅程。這陣子晚上散步,劉達勇喜歡看天上的星星,閃爍如同雷達屏幕上跳動的波光,“那閃爍的波光,已然成為牽挂”。
這一刻,大海深處的擔杆島,戰友們也在想念著這名老兵。(易文豪)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- 評論
- 關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