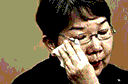今日龍須島灘頭。高洪超攝

日軍在龍須島附近海面組織登陸。高洪超提供
前人經歷的甲午,是私利之爭的悲局﹔后人所知的甲午,亦是私利之爭的碎片。
品甲午之痛,莫過於此……
此時駐足榮成灣的灘頭,真實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,在風中交織,一片汪洋都不見,知向誰邊?
只是那個日子,至今讓人揪心——1895年1月20日,日軍在榮成灣登陸,打響了埋葬北洋水師的最后一戰。
人是歷史的劇作者,也是歷史的劇中人。在以生死為代價的殘酷戰爭中,可以看到最敏銳的智慧、最狡詐的權謀,甚至平日裡最難捉摸的人性,在此刻也往往能清晰洞見……
在這一幕悲劇中,有兩個人物至今讓人痛惜——
其一是丁汝昌,其實他已是“囹圄之身”——開戰以來,這位在前線浴血奮戰的指揮官,收獲最多的,竟是朝堂上雪片般的彈劾奏折。
1894年12月17日,清廷諭令將丁汝昌革職查辦。若不是海陸將領聯名上奏:丁汝昌“日夜訓練師船,聯絡各軍,講求戰守”,如果抓了,“軍民不免失望”。他或許就是另一個“岳飛”式的下場。
也許他打仗確有過失,然而遠在甲午戰爭打響之前,清廷內部“利益地盤”的爭斗就已成水火之勢。那位以實業聞名的清末狀元張謇,在給他的老師、清流黨首翁同龢的密信裡早已說得露骨:“丁須即拔……可免淮人復據海軍。”
另一則是李秉衡,這位手握3萬重兵的山東巡撫,明知日軍已經在威海衛東側的榮成灣登陸兩天,卻一口咬定西側的煙台一帶要固守,遲遲不發援兵。
這就是並肩作戰的友軍?這就是死生相托的同胞?后有學者評價李秉衡是不懂兵略,沒有搞清日軍動向,其實不然。
北洋水師剛剛覆滅,李秉衡就呼應朝堂清流之議,冷酷地上奏:丁汝昌“戰敗死綏,僅足相抵”。
論史及此,威海水警區司令員王琦不禁拍案:“該殺的反倒是李秉衡這種寧安一己私利、罔顧國家安危的人!”
甲午之時的中國,“帝后兩堂暗斗於內,翁李兩黨傾軋於外”。戰場上,湘軍、淮軍、綠營各成派系,挾國家利益而爭權,即使是海軍內部,也是南北分域,勾心斗角。
還是日本人寫得尖刻:清國“兵民處於四分五裂狀態……直隸兵敗而兩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顧﹔北洋水師大敗而南洋水師不僅坐視不救,反而暗自嘲笑”。
看到這裡,再論甲午之敗,什麼戰法謀略的失誤,什麼船速炮速的落后,都不過是蒼白無力的開脫。
甲午之敗,殷鑒不遠,一己私利的“流毒”其實也是當前軍事斗爭准備的大敵,也正悄悄腐蝕著我們這支軍隊:
——軍種、單位的“本位主義”根深蒂固,聯合作戰、聯合訓練“貌合神離”,一唱三嘆。一位將軍想得更深:長期以來,我們一直批判“大陸軍”思想,真往深裡想,強調自身重要性的“大海軍”“大空軍”思想,難道就不存在嗎?”
——小到一顆螺絲的尺寸統一,大到三軍數據共享,條塊分割、自成體系,處處是壁壘,事事有藩籬。官兵們苦不堪言:“就像兩條高速路的交匯口是一座獨木橋,再好的司機也隻能踩剎車!”
在邁向強軍目標的今天,我們必須清醒地正視這個現實:對我軍戰斗力建設影響最大的,可能不是別人,可能不是觀念理論的落后、不是經費資源的限制、不是技術專業的不足,根本原因就在我們自己!
就是我們內心深處有意無意膨脹的一己、一隅的私利,遮住了我們的眼睛,使我們不能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准,不能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,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。
成員的自利,終將變為一個集體的愚蠢!什麼時候都隻考慮“我”,就沒有了“我們”。只是,這個“我”的確太強大太迷人——
那位被康有為稱作“中國維新第一導師”的翁同龢,卻因與李鴻章的私仇和政爭,1888年力主停購軍艦,1891年停撥海軍器械、彈藥經費。那位被譚嗣同譽為“尤能力顧大局”的晚清“四大名臣”之一的張之洞,在朝廷下令南洋水師支援時,卻故意為難,自貶南洋官兵“皆不得力”,逼著北洋水師派人接船,最終也未派一船助戰……
他們是那個時代最有遠見卓識的人,卻依然看不穿:自利無異於自殺,忘國終將會亡國。
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,終將葬送國家的利益、軍隊的戰斗力。駐守在這片海邊的某海防團團長楊偉峰,難忘戰爭史上的歷歷往事:二戰時日本陸軍與海軍分庭抗禮,甚至自造航空母艦和潛艇,至今被日本學界痛批“太平洋戰爭是自己打敗自己”。美軍以越戰和海灣戰爭中血的代價換來《聯合轉型路線圖》,跌宕起伏幾十年才跨過了利益藩籬。
不破藩籬,何以破敵!再多的嘆息和淚水,也不能告慰前人的鮮血。120年后,面對依然來自海上的威脅,如果我們還看不到強軍目標的大勢所趨,還打不破自利發展的狹隘格局,我們又怎能肩負起能打仗、打勝仗的擔當?!
蕭瑟秋風今又是,我們這個民族走向復興的雄心和夢想,不應再被“一己私利”的洶涌掩埋……(魏兵 王天益)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








 恭喜你,發表成功!
恭喜你,發表成功!

 !
!